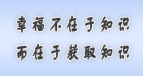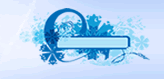《老王》的喜剧精神与淑世情怀
《老王》的喜剧精神与淑世情怀
江苏省宿迁中学 李彬
杨绛先生在《将饮茶·隐身衣》中说:“世态人情,比清风明月更饶有滋味,可作书读,可当戏看。”把世态人情当书读,当戏看,就必然有一种距离,而这种距离通常产生美感即喜剧性。杨绛的散文大都以时移事往的人事为题材,但作者决不因时间的推移而随意窜改历史的本真面目,反而是因着时空的距离、岁月的观照,更加客观地审察、评价、记录历史。杨绛向读者举起了生活的镜子:“给德行看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
《老王》是杨绛写于1984年的一篇散文,目前已选入人教版、苏教版、沪教版等多家中学课本,讲述的是杨绛一家人和善良的三轮车夫老王交往的故事,写底层劳动者在不幸的生活中不改淳朴善良的天性。该文都是平常的生活描写,没有任何传奇因素,杨绛却能从平凡的场景中找出可笑与荒谬。作为一位有深刻思想的作家,杨绛的幽默没有停留在引人发笑的层面,她关注的是透过笑声,使人看到隐藏的悲哀。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杨绛先生问“那里是不是他的家”,老王答“住那儿多年了”。这个回答有些答非所问,顾左右而言他,却又值得我们沉思。老王的这个回答包含丰富的潜台词:我没有家,家里有亲人,有温暖,有快乐,这里什么也没有,它只是我孤寂人生的落脚点。
《老王》的语言是机智幽默的,如果它平淡得就像一杯白开水,无色无味是不足称赞的。在写老王给我家送冰块时写到:“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前任”一般用在比较庄重的场合,比如“英国前任首相撒切尔夫人”。杨绛先生在此处用“前任”有诙谐幽默之感。同时,文章仿佛在说“老王”虽然在做“送冰”这样一件非常普通的事,但是他很认真诚信的态度值得尊敬,这在诙谐的外表下多了一分厚重。又如在写他在去世的前一天硬撑着身子给“我”送香油和鸡蛋一事时对他肖像的刻画,“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白骨”,作者用夸张的修辞凸显老王临死前消瘦无力的情形,非常逼真,还有点滑稽感,但读者是笑不出的,只会觉得心灵深处在隐隐作痛,只会为他知恩图报、至死不忘的善良的心而感动。杨绛的笑不是冷笑、嘲笑,也不是肤浅的滑稽、诙谐,而是“用泪水洗过的,所以笑得明净,笑得蕴藉,笑里有橄榄式的回甘”。
“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杨绛曾经说过:默存在哪,家就在哪。作为妻子,她不可能不知道自己丈夫的一条腿怎么就走不得路了。在这里,作者用了幽默的曲笔,含蓄地写出了丈夫遭受的非人遭遇。“不知怎么的”,貌似把文革中知识分子受迫害挨批斗轻描淡写,实则蕴含着备遭凌辱、无以言说的痛楚。如果说老王的眼睛残疾是身体不幸,那么“文革”中知识分子个人命运突然断裂,被打翻在地,直至“一条腿走不得路了”,又该是精神上怎样的“更深的不幸”?
艺术的最终品质是对人生的深切关怀,这就决定了真正的好作品在骨子里总有一种悲天悯世之心,真正优秀艺术家的“看”并不是事不关己的冷漠旁观,而是外冷内热、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是对人间真情的收束凝聚,使之更为厚重,而不是任其麻木消散。这也是作为一种高品位的审美品格的“幽默”与一般的街头巷尾取乐的“滑稽”的根本性差异。杨绛指出,奥斯丁小说好就好在具有“表里不一”性:“奥斯丁常常在笑的背面,写出不笑的另一面。”“看”的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就在于人世间的许多事有些看似可笑的其实并不可笑,反之倒是那些不好笑的情形却是很可笑。
在人妖颠倒的文革期间,人们不得已只好给自己披上一层狼的外皮,但其善良美好的人伦天性却是无论如何都扼杀不了的。“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可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杨绛)。疯狂年代里这种熠熠闪光的人性更凸显出人间情谊的美好温馨。《老王》在结尾写道:“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作者为自己在老王生前不曾真正了解他那颗金子般的心,没能尽自己最大力量帮助他改善处境,改变不幸而惭愧不安。“文革”爆发后,杨绛一家受尽了屈辱和蹂躏,夫妇先是被迫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后来女婿德一含冤自杀,全家被迫离家逃走……作者一家何幸之有?忆及那些“含泪”的往事,杨绛却淡淡地称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想起的却是“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我们怎能不感叹、敬重于杨绛先生那种豁达忘我、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
如果觉得《老王》的喜剧精神与淑世情怀不错,可以推荐给好友哦。
- 教材研究相关文章
-
- ·上一篇:谁说没有什么形象可言——《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之形象探索
- ·下一篇:杜甫《古柏行》原文、翻译及赏析
- › 细读《老王》,看杨绛散文的审美追求
- › 不幸·幸运·愧怍——苏教版高语课文《老王》的三个关键词解读
- › 善良是一种习惯——解读《老王》
- › 在“愧怍”中探寻《老王》主旨
- › 对《老王》教学设计的反思:国培计划作业
- › 《老王》教案设计(附教学反思)
- › 《老王》教学设计
- › 知恩图报,悲天悯人——我读《老王》
- › 《老王》的喜剧精神与淑世情怀
- › 不仅仅是悲悯——《老王》教学叙事
- › 光明的慰藉——品读《老王》中的人性美
- › 语文阅读教学要给学生留下空间——以郑朝晖《老王》课堂教学为例(...
教材研究推荐
- ·真实的力量——读《陈情表》有感
- ·“补白”:一个永不枯竭的文本解读话题...
- ·从文字中感受思想的火花——我教《荆轲...
- ·《香菱学诗》写作视角的阅读(黄行福)...
- ·为朵“小花”入“乐园”——解读《从百...
- ·让语文教材更符合教育规律
- ·谈《孔雀东南飞》中的体态语
- ·一篇迟到了几十年祭文——《记梁任公先...
- ·从几个维度看语文教材这个“例子”——...
- ·《记承天寺夜游》的主题探究
- ·“男女衣着”何以“悉如外人”?
- ·《侍坐》中的“现代教育”思想
- ·《背影》背后的深情
- ·从冰山原理谈《扬州茶馆》的文本细读
- ·闲人写给自我的便条——读苏轼《记承天...
- ·旷野中狼的长嗥——读鲁迅小说《孤独者...
- ·《念奴娇·赤壁怀古》正解
- ·司马迁的“阴谋”——《屈原列传》中的...
- ·《孟子见梁襄王》对话描写欣赏
- ·一首酬和两样情——试说刘禹锡是如何应...
- ·一声叹息——关于《行道树》的删节
- ·“边城“的那边是什么……——《边城》...
- ·让语文课本拥有最美的人生有何不可?
- ·李密:一位敢于向皇权说“不”的人
- ·《云南的歌会》美点寻踪(陈社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