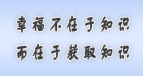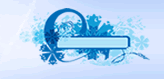《老王》的喜剧精神与淑世情怀
“我们从五七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谋生更加艰难,“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他才“可以凑合”维持生活。“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仿佛这样“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作者用幽默诙谐的叙述写来,乍读令人忍俊不禁,再读却不觉倍感心酸,仿佛看到了老王脸上满足的笑容,更看到文字背后杨绛微笑的面颊上一双盈盈的泪眼,这泪眼映照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社会忧虑。老王孤身一人且又身患重病,这无异于雪上加霜!病得不成人样的老王,还要挣扎着来到“我”家,作者着意刻画了他临终前的病态:瘦、僵。“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这句是总写,用“直僵僵”活画出老王病入膏肓、行将就木的样子,“镶嵌”更是用得特别,传神地刻画出老王清瘦、单薄、僵硬,没有一丝活气。“直僵僵”在全文出现了3次,他像一具“僵尸”,“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直”字写他僵直、艰难的动作,两手却都拿着东西——瓶子里竟是香油,包裹里竟是鸡蛋,如此珍贵、易碎的东西!老王这一路该是如何走来?巨大的悲剧感压在读者心头,催人泪下。
“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沃尔波尔)十年浩劫后,巴金秉笔直控“文革”的无道和对知识分子的戕害,季羡林围绕着个人的苦难进行回忆,韦君宜在耳闻目睹的基础上作灵魂深处的反思,杨绛却把这苦难的人生写成了生趣富饶的历练,用一些干干净净的文字写“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冒险记幸”,写人与狗的挚爱深情、劳动中的忙里偷闲,写看电影找不到回家的路、打井成功去沽酒等。那场不堪回首的精神灾难被朴实无华、不动声色的文字寥寥几笔带过,字里行间却以超常的镇定暗示人们:她的心曾经遭受了怎样的折磨!而这还只是“大背景”下的小点缀,“大故事”中的“小插曲”呢。她从不停留在一己悲欢的咀嚼上,也不以“文化英雄”的姿态大声抨击,而能够冷静地展示个人和周围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生态和灵魂,往往写出了事件的荒谬性,透出心中深刻的痛楚。
老子说:“言者不信,信者不言。”简约的笔墨、机智的叙述角度和淡泊的叙述语调贯穿在杨绛创作的全过程,而她对芸芸众生感情领域的测度和对东方哲学境界的体认又使其作品有一股风霜寒露中磨练出来的清气,蕴成一种优雅、静穆的中和之美。对于杨绛来说,让她觉得“可爱”的东西,正是那些“人性”的因素。她把“人”和“人性”看做是比“命运”更大的一个“谜”。即使是在是非颠倒的“文革”中,她始终未放弃对“人性”的寻觅和探求。杨绛由于长期从事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所以“文革”爆发后,她就被揪出来,按照她的话说:“我一写文章就‘放毒’,也就是说,下笔就露馅,流露出‘人道主义’、‘人性论’等资产阶级观点。”但她决没有胆怯畏缩,噤若寒蝉。相反,当她身处逆境,一旦有人对她报以同情的好感或帮助时,她总是满怀感激之情而久久难以忘怀。
细读《老王》,我们发现杨绛在看似平静的笔调中,凝敛着丰富复杂的内心感受与巨大的情感波澜。同是对“文革”浩劫的历史记录,杨绛的作品里没有号陶顿足,有泪也是“合上眼睛,让眼泪流进鼻子,流人肚里”;也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反而表现出一种情随事迁的平静与节制。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王德威教授的话说:“五四以来的女作家正如男性同僚一样,擅写涕泪飘零的故事。杨绛应是唯一以喜剧手法检视社会现实的女作家。……她冷眼纵观苍生,道尽市井男女张皇骚动的百态。”杨绛散文的喜剧精神和淑世情怀,源于父母亲的教育和影响,得益于长期的著译生涯(她翻译的西方名著《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都是充满幽默和讽刺的喜剧性小说)。另外,作为一位生活在20世纪动荡不安的政局和社会中的人,杨绛饱受各种各样的困厄和磨难,尤其是丙午丁未年遭逢的浩劫,也使她的喜剧意识更加鲜明,淑世情怀更加成熟。
苦难足以毁灭人,但苦难也能净化人,使人思考苦难,直面苦难,担当苦难。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只是一滩鲜血、一把眼泪,一个高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对于《老王》的意蕴,杨绛先生的心语也许就是最好的注脚。“喜剧精神”和“淑世情怀”已经渗透在杨绛先生的气质性情和生活方式之中,并成为她批评社会人生和获取生命体验的重要价值导向,因而也理所当然成为打开杨绛散文思想艺术奥秘的关键所在。
如果觉得《老王》的喜剧精神与淑世情怀不错,可以推荐给好友哦。
- 教材研究相关文章
-
- ·上一篇:谁说没有什么形象可言——《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之形象探索
- ·下一篇:杜甫《古柏行》原文、翻译及赏析
- › 细读《老王》,看杨绛散文的审美追求
- › 不幸·幸运·愧怍——苏教版高语课文《老王》的三个关键词解读
- › 善良是一种习惯——解读《老王》
- › 在“愧怍”中探寻《老王》主旨
- › 对《老王》教学设计的反思:国培计划作业
- › 《老王》教案设计(附教学反思)
- › 《老王》教学设计
- › 知恩图报,悲天悯人——我读《老王》
- › 《老王》的喜剧精神与淑世情怀
- › 不仅仅是悲悯——《老王》教学叙事
- › 光明的慰藉——品读《老王》中的人性美
- › 语文阅读教学要给学生留下空间——以郑朝晖《老王》课堂教学为例(...
教材研究推荐
- ·真实的力量——读《陈情表》有感
- ·“补白”:一个永不枯竭的文本解读话题...
- ·从文字中感受思想的火花——我教《荆轲...
- ·《香菱学诗》写作视角的阅读(黄行福)...
- ·为朵“小花”入“乐园”——解读《从百...
- ·让语文教材更符合教育规律
- ·谈《孔雀东南飞》中的体态语
- ·一篇迟到了几十年祭文——《记梁任公先...
- ·从几个维度看语文教材这个“例子”——...
- ·《记承天寺夜游》的主题探究
- ·“男女衣着”何以“悉如外人”?
- ·《侍坐》中的“现代教育”思想
- ·《背影》背后的深情
- ·从冰山原理谈《扬州茶馆》的文本细读
- ·闲人写给自我的便条——读苏轼《记承天...
- ·旷野中狼的长嗥——读鲁迅小说《孤独者...
- ·《念奴娇·赤壁怀古》正解
- ·司马迁的“阴谋”——《屈原列传》中的...
- ·《孟子见梁襄王》对话描写欣赏
- ·一首酬和两样情——试说刘禹锡是如何应...
- ·一声叹息——关于《行道树》的删节
- ·“边城“的那边是什么……——《边城》...
- ·让语文课本拥有最美的人生有何不可?
- ·李密:一位敢于向皇权说“不”的人
- ·《云南的歌会》美点寻踪(陈社教)